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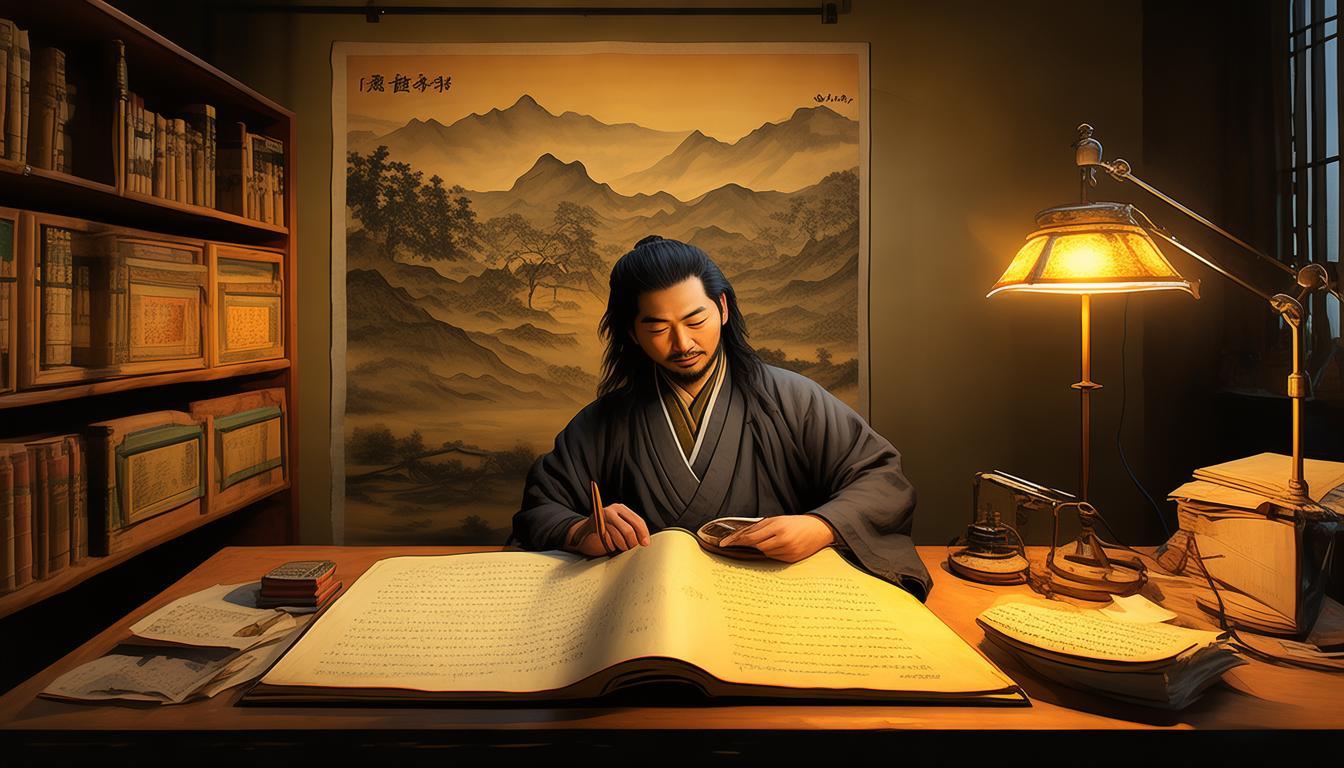
在对《史记》的研究过程中,关于“河山之阳”及“河山”的释义问题引发了诸多探讨。这不仅牵扯到千古史学名著的解读准确与否,而且关乎对司马迁当时所描述地理概念和历史背景的理解正确与否。通过深入分析《史记》三家旧注等相关内容,能够逐步揭开这些释义的真实面目。

《史记》三家旧注里,唐开元年间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对“河山之阳”作出了简单解释。张守节将这里的“河”特指为黄河,并以此对应太史公所说“河山”之“河”。然而他把黄河北岸与龙门山南坡来对应“河山之阳”,完全不符合常规中“山南水北为阳”的通例。这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寻找对于此说法的合理解释。

与此同时,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“河山”二字的释义又与张守节的解读产生了矛盾。文中提到“河山以南者中国”,若按照张守节将“河”对应黄河、“山”对应特定山的解释,就会得出“三晋、燕、代”不在“中国”之地的荒谬结论。但司马迁先描述“及秦并吞三晋、燕、代”再说“自河山以南者中国”,表明“三晋、燕、代”必然属于“河山以南”。所以张守节此注解有明显的不妥之处。

实际上,从《史记》文本中还能探究出“据”这个字在表述地理界限时当理解为“凭”“靠”“按”“压”。“秦北边长城起自黄河岸边,然后依傍阴山东行至辽东”,这一地理状况表明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“河山以南”的“河”指阴山西侧的黄河,“山”指阴山。这里“河山”是代指中原政权的北部国境线。

明了“河山”代指秦汉帝国北部国境线后,就要思考“河山”之阴阳具体表述的内涵。理解这一阴阳可能涉及到文化、地理以及司马迁自身观点等多方面因素。如今,回过头来看司马迁说自己“耕牧河山之阳”,这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宣告,可能是在表明其出生于文化比较发达地方之意。